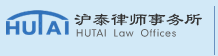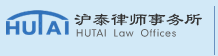谨慎解释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兼谈经济违法行为的刑法介入
肖中华
非法经营罪是修订刑法在废止过去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后新增的一个罪名,立法初衷显然是要将过去由投机倒把罪评价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类型化、特定化,并同时增强刑法规范的“安定性”,使非法经营罪的罪刑规范不致像以往的投机倒把罪那样被恣意解释而轻易入人于罪。但是,非法经营罪创立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主要的争议是刑法第225条第(三)项(经1999年《刑法修正案》修正后的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何认定?争议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个罪的犯罪构成问题,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触及了刑法基本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在刑事司法活动(广义地包括有权司法解释的制定)中如何正确运用刑法解释的规则与方法,以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特别是对于刑法中的空白罪状如何合理解释?对于普遍运用空白罪状的经济犯罪而言,如何解释刑法规范、理解空白罪状的意义,归根结底是一个刑法介入经济违法行为的广度、密度和力度问题。当然,具体而言,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比如,空白罪状与行政法规的关系;认定经济犯罪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本文主要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及其认定入手,结合当前司法解释有关内容和司法实践的一些做法,发表如下看法:
第一个问题,解释“兜底”条款,应当符合同类规则。由于刑法调整新型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专业化,从保护法益出发,像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这样“兜底”条款在立法中出现,本身无可厚非。运用“兜底”条款的目的在于严密法网,堵截法律漏洞。当然,由于这种刑法隐形规定,字面上没有直观地规定构成要件内容,构成要件要素必须通过对内容的分析才能确定,因而存在不明确性的缺陷。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是否合理正当,就显得十分重要。究竟如何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呢?我认为,按照同类规则,其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该项所称行为必须是一种经营行为,亦即,必须是有成本投入、追求利润或者说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2)该经营行为属于非法行为,但“非法”的内涵是特定的,即与刑法第225条前三项行为属于“同类”。从刑法第225条前三项的规定来看,不论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还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及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等行为,非法的内容都是违反国家有关经营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因此,第四项行为也应具有这一特征。(3)该非法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值得刑罚处罚。基于上述分析,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经营出版物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以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经营国际电信、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均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是不符合同类规则的,因为即便根据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属于非法的经济活动,但与国家经营许可制度没有关联。另外,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这一规定同样是违反同类规则的,因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国家关于市场交易的价格管理秩序,但与国家关于经营许可管理制度无直接关系。
在司法个案中,违反同类规则的解释时有发生。当然,不合理的解释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前者如将买卖伪造的金融票据这种实际上法无明文的行为认定为伪造金融票证罪或票据诈骗罪的共犯,后者如将无烟草经营许可证者调济香烟余缺、赚取微利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我认为,违反同类规则的解释结果,必然是使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患上“肥胖症”,最终使非法经营罪成为新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
第二个问题,为区分经济犯罪中此罪与彼罪,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当遵循“内涵越丰富的要件越应被优先考虑为评价行为的标准”的原则。从目前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地方,为了严厉打击盗版活动,司法机关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这种做法有功利的动机,这就是因为刑法第218条规定的刑罚较轻——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法定最高刑不过三年有期徒刑;而且,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该罪构成要件“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对个人来说是指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对单位来说是指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而如果对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则对行为人的定罪的数额标准要求明显较低、刑罚处罚明显要重,因为按照司法解释的的规定,非法出版物的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违法所得在2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问题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能否用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来评价?我认为不能,因为刑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这个罪的构成要件比任何其他罪(包括非法经营罪)都要丰富、全面地描述了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由此可以断定,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如果其达到了犯罪数额标准,就应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否则即应认定无罪,而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的精神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只有对于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第1条至第10条规定的非法出版物的,才有可能根据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处理。
第三个问题,经济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要不要以空白罪状所指的法律、法规中有刑事责任规定(一般表述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我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但是,这并不是否定经济犯罪的“二次违法性”,恰恰应当强调,作为法定犯或曰行政犯的经济犯罪,其构成必须以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为前提,否则就失去了处罚的前置依据,也不符合空白罪状在描述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特性。因为是否存在作为前置依据的法律、法规,与这些法律、法规中是否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并非一事。存在作为前置依据的法律、法规,解决的是开放构成要件内容的补充,刑法中开放的构成要件内容若无补充,认定犯罪便没有依据;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是否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并不影响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定罪量刑,因为只要这些违法行为通过刑法空白罪状的表述而具有刑事违法性,其法定刑自然均由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来设置。在我国,附属刑法并不规定法定刑,是否是刑法的渊源本身值得研究。总而言之,“罪刑法定”的“法”应当是指刑法,而不包括其他法律、法规;对于空白罪状描述的犯罪构成而言,其他法律、法规也只具有对构成要件进行补充的功能。所以,其他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刑事责任条款,只要这种经济违法行为依照刑法(空白罪状)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就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即便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但在刑法中没有罪刑规范,则属于“法无明文规定”、虚设刑事责任的行为,不为罪。
值得研究的是,经济、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的新内容,能否用来补充刑法中的开放性构成要件?比如,修订刑法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某个法律或国务院制定某个法规,宣布某种经营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违者即属非法经营行为,那么,这种在修订刑法通过当时并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可否作为非法经营罪的情形?我认为,空白罪状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维护刑法相对稳定性的功能,因而为实现空白罪状的功能,对上述问题应当予以肯定的回答。当然,在个案中,应当注意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来源:华东司法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