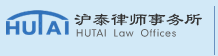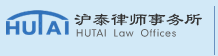|
影视剧改编权探讨
金忠德
本文所谓影视剧改编权,专指影视剧编剧将合法取得改编权的文字作品,如小说等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权利。现将改变表现形式的改编与不变表现形式的作品修改,及改编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结合办案体会,依据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作一探讨。
公开发表的文字作品,如小说等,经常是影视剧二度创作的蓝本,但由于文字作品的表现形式和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不同。因此,各自必须遵循的艺术规律不同,创作方式不同。依据不同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品,既使是小说母本的改编本,也必然会有内容、情节,甚至人物场景的改动。而影视剧改编涉及的小说原著内容、情节的改动,不时会引起原著作者的异议。在上海法院受理的版权纠纷案中,就有小说作者指控影视剧编剧“擅自修改”小说内容、情节的案例。诉诸法律,澄清问题,无论对原著作者还是影视编剧,都有划清法律界限,明确各自权益,保护正当创作的实际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是明确“修改”与“改编”,“修改权”与“改编权”的唯一法律依据,是明晰基本概念,解决影视剧改编法律纠纷的首要前提。
著作权法第十条归纳了著作权的五项权利,其中第三项是修改权,第五项是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改编权是第五项权利中的一种演绎权。修改权和改编权是不同类型的权属,其法定涵义不同,适用范围、对象不同,法律效力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
修改:意指改正文章、计划等里面的错误、缺点等。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报社、杂志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这条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修改不变更原著的表现形式,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修改权是在作品原表现形式范围之内的,越出这个范围,就越出了修改的法定内涵。修改的对象当然也可以是内容、情节,但因修改权是著作权中人身权之一,他人实施作品内容的修改,依法必须征得作者的许可。因而修改权中的修改,归纳其本质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1、在作品的既定表现形式之内;
2、除作者自行实施外,相对他人是一种授权许可。
改编则不然。改编,意指根据原著重写,体裁往往与原著不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八项将改编的法律涵义明确为:“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在取得改编权的前提下,如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很显然,条款中“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是指表现形式的变换。而随着表现形式的变换,“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只能是指作品的内容、情节等的必要改动。但此条最具实践意义的是其中“必要的改动”可以不经原著作者的同意而“视为已同意。”这是改编权利人法律允许的改动内容、情节的权利,是改编权的主要内涵之一,否则,改编作品的“独创性”就无从谈起。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改编相对于修改的自身特征:
1、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
2、必要的改动是改编权下的一项法律许可的权利。
通过对修改与改编的法律分析,对比两种特征,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两者的差别:
1、修改在作品的原表现形式之内 ,而改编则改变表现形式;
2、修改是授权许可,合理、必要改动则是改编权范围内法律授予改编者的一项权利。
3、修改不变更著作权主体;而改编则重新创造出新的作品,改编人是新的、独立的著作权主体。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原著作者认为影视剧编导仅仅获得改编权,而不能对其内容、情节进行改动,否则是侵犯了原著的修改权,属擅自“修改”作品内容、情节,是典型的混淆法律概念,曲解法律条文,是将改编权中必要改动的编导权利拉扯进修改权中的授权许可内,抹煞了改编的改变表现形式的特征及其由此必然产生的必要改动。
从法律权利的意义上看,改编权中的法律规定的许可可以对抗原著作者修改权之授权许可。它排除任何人包括原著作者的干涉而独立存在,并由改编人独立行使。从法律后果上看,修改仅仅是原著的某种完善。而改编,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获得独立的、不受制于原著的著作权。
既然改编权有法律许可的必要的改动,那么原著和改编作品之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从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看,这种差异从表现形式到内容情节无处不在。改编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是原著的异化,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不同于原著的新创作的部分。相对原著,改编作品的新创作必须有新意,有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抄袭和照搬不能成为改编。改编作品唯一应当遵守的,是第十三条结尾“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的规定。这条规定作为改编的一条原则限制,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那就会发生令人遗憾的情况。如有人指责把品位低下,消极灰暗的原著改编成另一表现形式的格调高雅、积极向上的新作品是“歪曲篡改”,会发生优秀作品“侵犯”了低劣作品的完整权的问题。这在实践上会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错误,会使人误解法律的公正和合理。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虽然没有对“歪曲篡改”作出解释,但我国承认和参加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六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损害行为。”这条规定清楚地在歪曲篡改前面加上了“有损其声誉”的限定词,为“歪曲篡改”与否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评判标准。改编作品在声誉上劣于原著的,就是有损于原著声誉,就构成了歪曲篡改。相反,改编作品在声誉上高于或者优于原著的,那就是必要的改动。由此可知,影视改编作品如果在声誉上劣于原著的,造成了事实上的不良影响,才能构成对原著的歪曲篡改,才会有“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假如仅就改编作品和原著的差别而论“保护作品完整权”,那任何一部改编作品都是侵权作品,任何授权改编都是对自己作品完整性的自我侵犯。如此改编,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影视剧改编者,原著作者也会将是否“有损其声誉”作为衡量是否“歪曲篡改”的标准。有小说作者称编导的改编“损害了作者的声誉”,“使作者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构成了对原有作品的歪曲篡改”。专业人士也在报端著文,引用伯尔尼公约第六条第二款中“有损其声誉的歪曲篡改”的规定,论证“歪曲篡改”的法律依据。可见,原著作者和影视剧改编者对原著及其作者声誉是否有损,作为歪曲篡改与否的标准和界限是有共识的。
确定一条公正的、公认的标准,对于划分必要的、合理的改动和歪曲篡改之间提供了明确的界限,对于防止动辄以歪曲篡改非法干扰合法改编的再创造提供了法律屏障。同样,对影视编剧也划定了一条改编的下限。相对原著而言,改编作品格调低下,艺术质量粗劣,社会声誉明显差于原著的,原著作者有理由认为改编构成“有损害声誉的歪曲篡改”而要求改编者承担侵权责任。
简言之,在原有表现形式上的修改与改变表现形式的改编,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艺术活动。遵循的艺术规律不同,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如果仅凭内容、情节的改动,就将影视改编作品视为“篡改”小说,那么至少是分不清电影、电视与小说的差异。至于改编的度,首先应当是原著作者和改编者根据改编的需要加以框定,并以合同明确之。如未能有书面约定的,则应有某种形式的原著作者对改编作品的认可。如果除允许改编外什么约定也没有,事后原著作者对改编作品持有异议而发生纠纷,那么按照司法实践,只能由原著作者负责举证“歪曲篡改”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了。以往判例证明,除非原著作者能够证明“有损其声誉”,否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 |